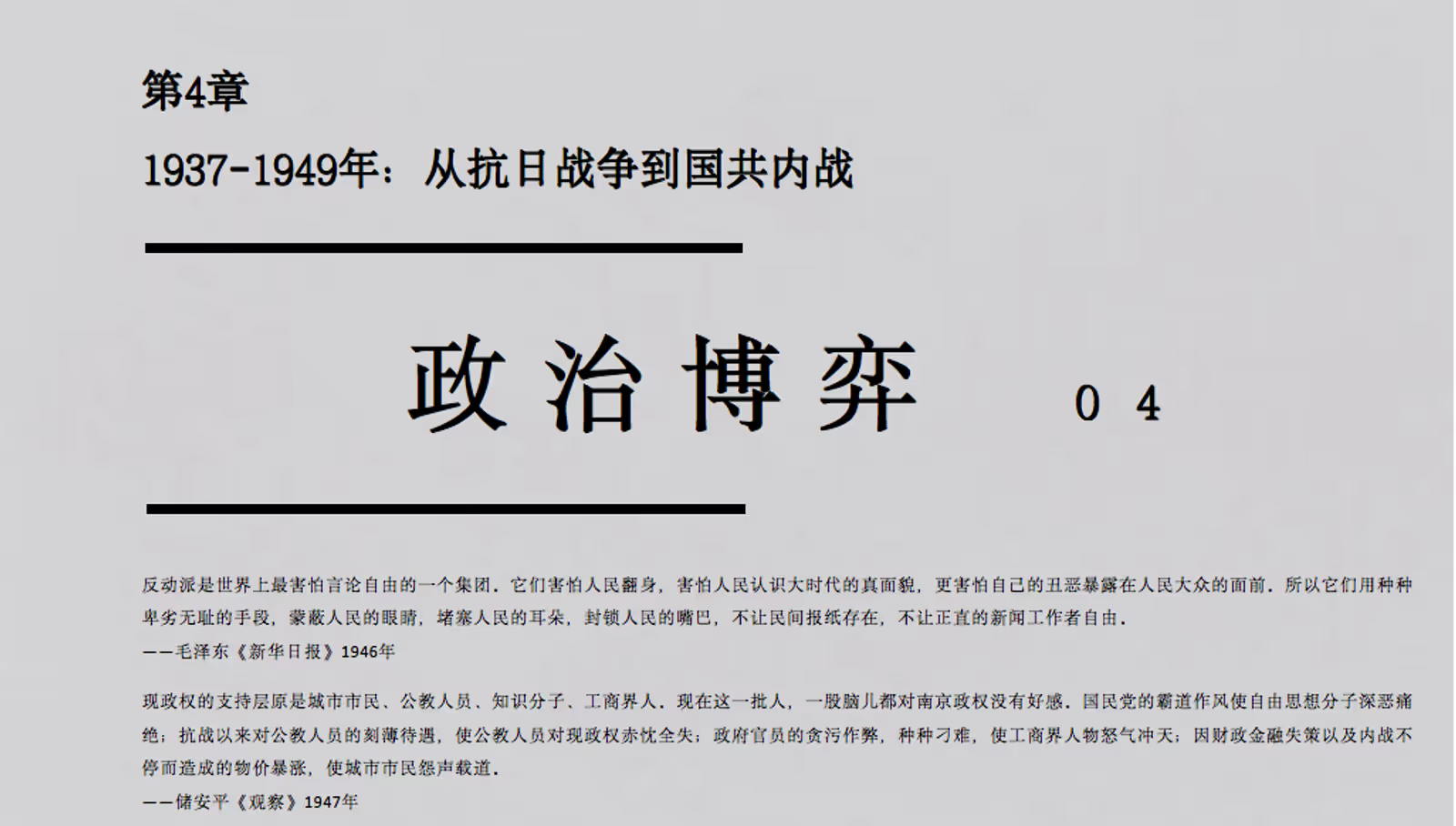
苏军对东北经济合作条件的坚持,中共对国军接收东北的阻挠已经逐渐为全国民众所知晓。1月16日,国民政府派出东北参与接收工作的经济部东北接收员张莘夫与苏方接洽抚顺煤矿接收事宜,于当晚从抚顺回沈阳经李石寨车站,张与一行随员被苏军和中共杀害[1]。对此,国民党认为这显然是苏军与中共所为;中共在内部指示(2月25日)统一口径是国民党“勾结日本人制造张莘夫惨案,以为反苏反共的借口”;苏联大使彼得罗夫于2月27日答复重庆外交部:“张莘夫被害系暴徒所为。”[2] 当张莘夫惨案于月底被披露出来之后,从2月22日至3月初,由重庆开始,全国主要城市爆发了反苏反共的大规模游行。人们对苏军逾期未撤离、雅尔塔会议中关于“苏联应恢复以前俄罗斯帝国之权利”等条款、苏军对东北提出的经济合作超出中苏条约规定的要求、苏军对东北工矿设备的拆卸搬运回国、苏军支持新疆少数民族起义、中共对国民党军进入东北接收工作的阻止、对中共于2月13日提出的关于东北四项要求[3]的普遍不满,张莘夫惨案成为导火索之一。2月16日,在重庆的部分东北人举行反苏游行,之后引发中央大学、重庆大学等重庆20多所大中院校2万多学生的反苏反共游行。学生们高呼口号要求彻查张莘夫惨案,苏军立即退出东北,中共应即爱护祖国。23日,上海圣约翰等72所大众学校的学生走上街头游行,在苏联驻上海领事馆呼喊口号:立即撤退东北苏军,我们要求完整接收东北,打倒出卖祖国的任何政党,打倒赤色汉奸。以后,北平、南京、昆明、郑州相继爆发游行示威。在游行队伍和各类宣言里有不少知名人士和知识分子加入:王力、宗白华、沈从文、吴大猷、陈序经、冯友兰、汤用彤等110位教授(西南联大关于东北问题的宣言);傅斯年、王云五、宗白华、储安平等20人(《我们对雅尔达秘密协定的抗议》);2月23日,民盟黄炎培、沈钧儒、张君劢和彭一湖在上海联名发表四点主张:
(一)我人主张用全力保护我国一切主权,不能超过中苏友好协约之规定,使权益上有所损害。(二)我人主张应继续要求苏联依照约定撤兵。(三)我人主张东北一切内部纠纷,应依照政治方式协商解决。(四)我人对任何方面,反对以中国人打中国人。 [4]
3月7日,有陈岱孙、顾颉刚、齐思和等40余位文化名人联名发表意见书:“我们不能容忍除中国国民政府以外,在东北与察热及任何地点有任何特殊政权的存在,我们也不能容忍中国政府于相互的履行中苏条约以外再有任何辱国的让步。”国共双方的媒体对这个事件均有不同看法,2月24日,蒋介石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各地学生对东北问题游行示威,实为俄国在廿五年来未有之教训,自此应即阻止矣,不可扩大。”[5] 2月26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一篇文稿写的几段话中,认为游行事件是“反革命示威”[6]。
3月1日至17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六届二中全会,会上的议题很多,关键的主题仍然是对政协会议文件的审核、对中苏条约执行状况的分析以及东北问题。会上争吵不休,并暴露出国民党党内严重的意见分歧,蒋介石希望通过党内会议统一思想,以为落实政协会议改组政府做准备。当党内有人严重提出必须修改宪草原则时,蒋介石同意了。孙科对修改做了解释:“所有对于《五五宪草》之任何修正意见,皆应依照《建国大纲》与五权宪法之基本原则而拟订,提出国民大会讨论决定。” 一开始,中共谈判代表周恩来同意了由宪草审议委员会与政协综合小组举行的联席会议对宪草原则的三点修改,然而延安否决了周的修改。胡乔木在3月19日的《解放日报》上发表了《评国民党二中全会》的文章里说:国民党提出“制定宪法应依建国大纲为最基本依据,这一规定本身就充满了一党专政的臭味。参加政协会议的各党派从未也永不可能同意国家的宪法应以某一党的某个什么文件为最基本之依据。”结果,中共颠覆了国民党提出的制宪依据,而由政治协商会议来制定宪法,这个政治程序与逻辑显然涉及现有的国民政府的合法性基础问题,国民党显然不能同意。4月,第四届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决议:“中共解放区之特殊组织,应予取消,以收统一团结之实。”中共对此也同样反对,认为破坏了政协精神。3月12日,在重庆政府没有接到任何知会的情况下苏军突然开始撤离沈阳,国军次日进占该城市,现在,只剩下国共双方之间讨论东北的接收问题,严峻的冲突使得该问题成为二中全会上争论的重要问题,党内就与苏联的外交和与中共的政治问题而出现指责、埋怨、解释没有产生一致意见。结果,二中全会希望解决的两个焦点问题——宪草原则与东北问题——均未解决。
与之同时,会上关于“官僚资本”问题的讨论表明了这时国民政府面临的经济与制度困境。“官僚资本”这个并非专门的经济学术语在当时涉及到多种形式的国家资本:官僚参股或投资(例如宋氏家族的企业),官僚使用或运用的国营资本(实为可以权力寻租的国营企业)以及其他形态受官僚支配和控制的私人资本[7]。可以想象,一党治国的体制很容易给予官僚、权贵、豪门机会以权谋私,将国营企业变为个人、特殊集团的私产或谋取非法利益。抗战后期,人们已经开始了对官僚资本恶果的指责,战后没收的日伪产业不仅使国家资本迅速增长,也为那些不法官僚豪门提供了控制与豪夺的机会,舆论普遍给予了批判。例如CC系控制的《中央日报》不断发表文章予以抨击:“官僚资本操纵整个的经济命脉,且官僚资本更可利用其特殊权力,垄断一切,以妨碍新兴企业的进展。所以代表官僚利益的官僚资本,如果不从此清算,非仅人民的利益,备受损害,抑且工业化的前途,也将受严重的影响。”[8] 在六届二中全会上,不少与会者对当前的经济问题极为忧心,对行政院长宋子文在政治报告只字不提官僚资本的问题极为不满,并将此时东北接收过程中出现的官吏贪污等现象一并牵扯出来。在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和陈立夫共同整理的《党务革新方案》中,官僚资本已经被提升到“为全国所痛恨,亦为全党所痛恨”的政治高度。历史学家傅斯年认为此时中国的国家资本“糟的很多,效能两字谈不到的更多。推其原因,各种恶势力(自然不以孔宋为限),豪门把持着,于是乎大体上在紊乱着、荒唐着、僵冻着、腐败着。恶势力支配,便更滋养恶势力,豪门把持,便是发展豪门”[9]。
1947年3月21日至23日,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召开,经济问题成为焦点,之前一个月,上海爆发的黄金风潮——黄金、美元暴涨——引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宋子文为此下台,在会上,不少与会者要求必须对公债舞弊追责,惩办官商与官僚资本,没收财产,惩办贪污,否者“国民党是要亡的”(谷正刚)。由宋子文实行的金融开放政策,开放黄金外汇市场,是彼时财政金融的措施之一,保持其有效性最基本的是市场预期心理的稳定和政治社会上的稳定。通货膨胀、与中共之间的内战、政府治理信用的下降以及战后本身所需要的社会稳定不足,最终导致黄金风潮的爆发。彼时就有评论:“根本上讲,物价的病根在于通货,通货的病根在于内战。内战不停,生产不能进展,通货不能停发,物价便无法收拾。黄金政策,即使改弦更张圆滑的运用,还只能减杀物价的波动,并不能根本解决物价问题.”(严仁赓:《检讨黄金政策》,《世纪评论》第8期)1948年下半年的金融崩溃的真正原因即是国民党政治与经济治理的全面失效进而失去信用的结果。
尽管中共继续采取了“边打边谈”的策略,中共在谈判过程中保持了对美国态度的谨慎,中共清楚美国的价值观,因此,在与美国交换意见的时候,尽量保持“三民主义”和“民主”“自由”这样一些美国喜欢听到的词汇,例如周恩来在1946年1月31日给马歇尔的信中有这样的策略表述:
在目前中国,采取社会主义所必须之条件尚不存在,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上固以社会主义为吾人最终之目标,惟在最近之将来,并无付诸实现之意,亦不认为有即付实行之可能。吾人所称将循美国之路径者,乃指获致美国式之民主与科学,并使中国采行农业改良、工业化、自由企业及个性发展等,庶几能建立一独立、自由、繁荣之中国。余兹拟奉告轶事一则,阁下或亦乐闻也!最近谣传毛主席将往游莫斯科。毛主席闻知而笑,且以半说笑话之态度曰,倘渠若出国休假(照其目前健康情形,休假于彼甚为有益),则更愿前往美国。因渠认为在美国能学得甚多有益于中国之事物。 [10]
尽管马歇尔在3月初访问延安时获得了毛泽东关于贯彻停战并着手政治协商和整军方案,但他更不用说在美国的杜鲁门完全没有体察出蒋介石和毛泽东的焦虑和不安,事实上,蒋介石只需要美国的武器与军需,并不希望美国过分的政治插足,这无异于干涉内政,耽误了时间;至于毛泽东,和平条件下的讨论可以尽量拖延时间,如果有有利于中共的好处,当然不是坏事,但是,中共不过是在用时间换取未来的空间,以尽可能拥有充分的时间准备进军东北。冲突根本就没有停止,在马歇尔3月11日返回美国准备为国民政府办理五亿美金贷款的次月,国共两党将战斗升级到相当规模,4月14日,苏军撤离长春,18日,中共进占该城市;这天,刚从美国回到重庆的马歇尔得知消息说:“中共进攻并占领长春是对停战令的重大违犯。”[11] 事实上,在马歇尔回国之前,周向马作了停止冲突的保证, 现在,周的解释是国民党不顾停战协议占领了“我们七个城市”,所以中共要占领长春。周恩来每一次谈判和事务解释上所表现出来的精敏异常的外交技术给马歇尔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中共没有停止进占的计划,刘少奇告诉重庆谈判代表团,哈尔滨苏军于24日撤退完毕,“我军可于其撤退当日或次日进占”[12]。此时全国民众对战争已经痛恨悲愤之至,5月22日,民盟张君劢、黄炎培、沈钧儒、张伯钧、梁漱溟联名致电蒋介石和毛泽东,谓东北战争“外失盟邦,内失全国人心”,同时提出三点国共两军分别不再进兵和撤出长春的方案。最后,长达数月的四平战役结束,政府军收复四平街,考虑到中共军力不济,毛泽东最终决定撤出长春,23日,国民党军队占领了这个中共本来想作为首都的城市。当月,国民政府将首都迁回南京。四平战役之后,马歇尔失去了中共的利用价值,而中共为了取得充分的准备时间,仍然利用马歇尔的调停,继续与看上去强势的国民党进行谈判,周恩来采取拖延之术,目的在于推迟内战的全面爆发。与之同时,中共通过宣传,强调国民党的独裁与卖国,而中共是争取国家和平独立民主的真正力量,在7月间,中共甚至公开指责美国对华军事援助实际上是对中国内政的武装干涉。6月中旬,蒋介石告诉他的军事将领,国民党最后的敌人“就是共产党”。7月2日,蒋介石与周恩来进行了最后一次面谈,无果。9日,周恩来继续用一种看上去为人们普遍能够接受的站在中国人而不是党派的立场对美国教授说:“美苏关系的不好,常影响到中国的内政,这是事实。但从中国的立场看,并非没有办法可以自处了。如果国民党的政府是聪明的话,它应该自动地负起桥梁的作用,不要甘心地做一国的工具。或者如果中国的国民政府改组成联合政府了(按照政协那样去做),与一切盟国都保持友好关系,则中国不致完全受一国的影响不能自拔,而且可以反过来积极影响国际间的合作。”[13] 周恩来当然不会去公开与人讨论苏联在中共的后面究竟有什么许诺与支持。蒋介石非常了解这位曾经的部下今天的中共领导人,他不再对中共抱有丝毫的希望。7月7日,中共在《“七七”九周年纪念宣言》里明确指责美国与国民政府,没有顾及还没有离开的马歇尔的面子,马已经知道自己失去作用,即推荐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为驻华大使。7月14日,蒋介石与宋美龄赴庐山“避暑”实为指挥对共作战,苏北战事昨天开启。继7月12日李公朴之后,15日闻一多也被国民党杀害,发生在昆明的暗杀事件强化了中国知识分子对国民党的普遍不满,国民党失去民心的程度已经无以复加了,“李、闻事件”也导致美国国内不少人反对继续援助国民党蒋介石。在蒋介石驻庐山期间马歇尔有八次上山与蒋讨论停战,在来来回回的调停中,马的耐心接近尾声。
注释:
[1] 时任中共抚顺视为书记兼抚顺军分区政委的吴亮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写了一份材料:
国民党派张莘夫等人来接收抚顺矿务分局和抚顺煤矿。那时,我们的方针是对接收进行抵制,他们未能实现接权。不多几天,他们就走了,我们派人送他们出去。到了半路,来了电话,说是苏联红军军官要搞他们。我当时在电话上听了,摸不清情况。当时苏联红军部队驻抚顺,实行军管,红军的事,我们无权管,(我)听了就说,让他们搞去,没有提出反对,这是政策上犯了大错误。苏联红军指挥我们部队,说他们是坏人,把他们几个杀了。此事件给国民党利用作为进行反共宣传的一个口实,使党的政治影响遭受了损失,迄今每念及此,辄深为痛心。这一事件的重要责任,是作为地方党委书记的我,应当负责的。为此政策上的大错误,我受到东北局给的撤销工作处分,我作了检讨,并于1月底离开了抚顺的工作。(雍桂良等著:《吴亮平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20页)
[2] 《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第673页。
[3] 1946年2月13日,中共提出东北问题四项要求:1,改组东北行营;2,承认中共在东北的军队;3,对于东北各县民主自治政权应予承认;4,国民政府开入东北的军队应限制在一定数量内。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整理:《黄炎培日记》(1946年2月23日)华文出版社2008年版。
[5] 《蒋介石日记》,1946年2月24日。
[6] 参见《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90-91页。本书转引自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77页。
[7] “官僚资本”被认为最早出现在瞿秋白的《中国之资产阶级的发展》(1932年)中,从40年代初期开始流行。经济学界并不随意使用这个词汇。
[8] 青年远征军第二0八师政治部编印:《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二中全会辑要》,1946年,第114页。
[9] 傅斯年:《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陈昭桐主编:《中国财政历史资料选编》(第12辑,下)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第123页。
[10] 《抗战史料初稿》,第7编,《战后中国(二)》,第249-250页,附英文件。本书转引自李云汉:《中国近代史》三民书局2018年版,第497-498页.
[11] 《马歇尔使华》,第114页。转引 第436页。
[12] 《刘少奇年谱》(下卷),第37页。
[13] 《中国不要成为一国的工具》,1946年7月9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南京市委会编:《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