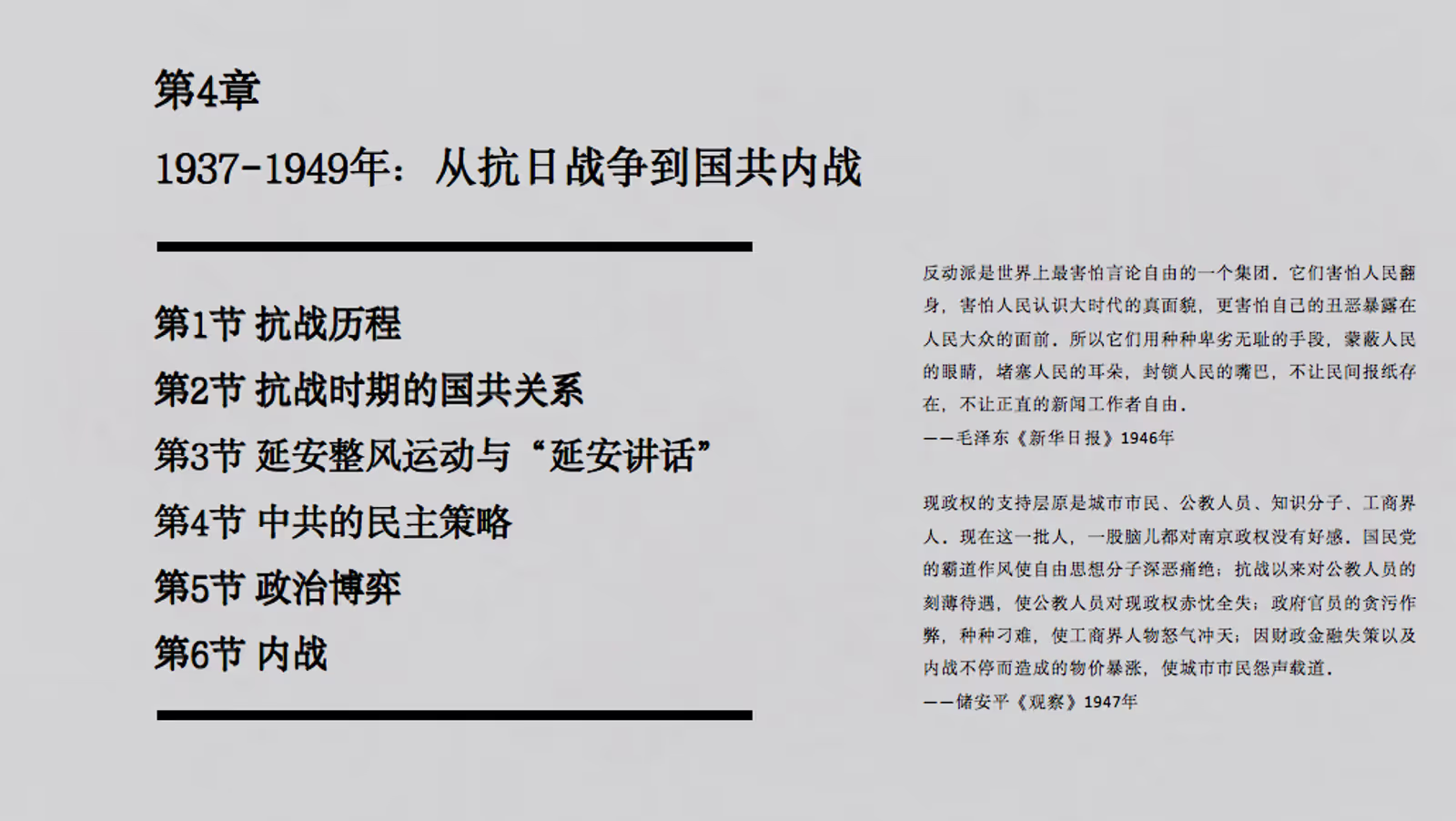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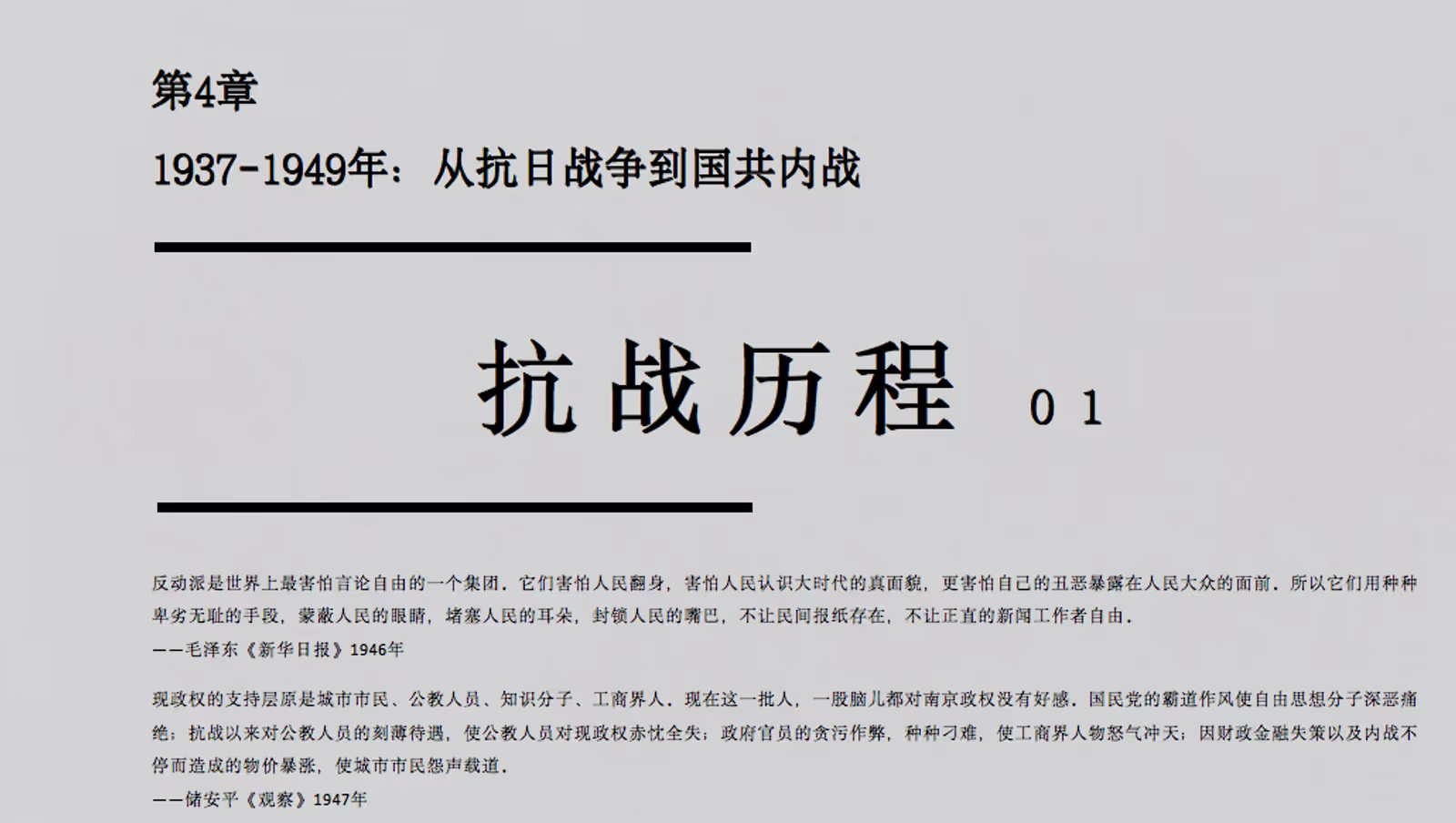
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在与文官集团不断争执与冲突之后,彻底不顾后者的意见的最终结果。那些少壮派军人抑制不住内心的武士道精神,在政客的激励与唆使下,他们自以为禀赋“神圣”意志,不断努力让军人在国家政治中占据支配地位,使文官们组成的政府变得可有可无,如果有人不予以服从,那么就是杀戮。从1931年春天开始,军国主义者实施了数次政治暗杀和权力颠覆,尽管受到审判,但是他们在法庭上的那种理直气壮的辩护态度却获得了不少的支持。1932年5月15日,当一伙少壮派军人冲进首相官邸杀掉首相犬养毅后被审判时,人们却用“爱国主义的献身精神”来褒奖他们[1]。事实上,部分高级军事领袖早就觊觎着中国,而一些政客与财阀与这些军事领袖的最终目的没有根本的差异,这就注定了日本人迟早会做出的冒险[2]。1936年,广田弘毅接替首相之职,他从1933年开始担任外相时,就表现出一种极端的态度,并延揽军队里的激进主义分子参与政府内阁。1936年,广田给中国提出的建议——其中第五条“日本向中国政府各部门派驻顾问”很容易让人们联想到“二十一条”——遭到中方拒绝,此时的中国已经有了几年的国民建设与抗战准备,因而敢于提出更为符合中国方面要求的条款,例如要求日本军队从冀察撤离,并抑制由日本人策划的自治运动。1937年初,接替广田的林铣十郎首相准备以一种缓和的方式与中国谈判。但是,西安事变之后的中国形势让国民政府有了更充足的自信与民族资源——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政治格局构成了坚决抵抗的力量。军国主义者们更换了内阁,对中国动武的声音不绝于耳,就在东京方面还多少处于斟酌的时刻,关东军[3]决定不顾一切推进军事行动。7月7日,他们借口寻找一名在卢沟桥(西方人习惯将其称为“马可·波罗桥”)附近演习后失踪的士兵,试图进入宛平县城搜寻,接防该城的第219团团长吉星文和县长王冷斋共同负责对此进行了具体的调查,告知日军未见所说失踪士兵。当中方拒绝关东军的要求时,后者于次日凌晨开始炮击城内和卢沟桥,并于当天进攻219团阵地,占领了由宋哲元第二十九军控制的宛平县城。这次,有备战安排的国民政府[4]不再需要用任何权宜之计去面对日本人的入侵和攻击,蒋介石于7月17日在庐山主持军官训练团和各界人士谈话会,他对在座发表演讲,如下是被人们经常引用的话:
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有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蒋介石宣布了四项解决事变纠纷的条件,核心是领土与主权独立不受侵犯。尽管蒋表明中国政府的立场是“应战而不求战”,但他号召“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而实际上,这时中国的军力与战争资源方面仍然远远不如日本。
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以及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都参加了庐山谈话会。知识分子的心境固然人各不同,但是,在蒋介石演讲的前两天(7月14日),吴宓的日记代表了一类文人之士的内心境况:
阅报,知战局危迫,大祸将临。今后或则(一)华北沦亡,身为奴辱。或则(二)战争破坏,玉石俱焚。要之,求如前此安乐静适丰舒高贵之生活,必不可得。我一生之盛时佳期,今已全毕。此期亦不可谓不长久,然初未得所享受,婚姻恋爱,事事违心,寂寞愤郁,痛苦已极。回计一生,宁非辜负?今后或自杀、或为僧、或抗节、或就义,无论若何结果,终留无穷之悔恨⋯⋯

对中共来讲,战争的全面爆发显然是中共取得合法地位的机会,7月23日,毛泽东代表中共积极而迅速表态:
共产党人一心一德,忠实执行自己的宣言[5],同时坚决拥护蒋介石先生的宣言,愿同国民党人和全国同胞一道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反对一切游移、动摇、妥协、退让,实行坚决的抗战。[6]
7月26日,日军占领廊坊,出于保护北平历史遗迹和用空间换时间的策略,国民政府主动撤出北平,7月30日天津沦陷。8月初,那些曾经与蒋介石对抗或矛盾不浅的各地将领参加了国防联席会,现在是民族存亡关头,军事领袖们已经决定捐弃前嫌,共赴国难,中共军事领袖也参加了该会。8月9日,守卫机场的航空委员会特务团哨兵打死欲强行进入机场的日本军人大山勇夫和斋藤要藏,日军随即组织海军、空军和陆军进入作战准备,12日,日参谋本部制定陆军派遣计划。从8月13日开始的“淞沪会战”标志着中日之间全面战争的开始:主张“先发制敌”的京沪警备司令官张治中次日发表讲话:“昨(13日)下午四时,日方军舰突以重炮向我闸北轰击,彻夜炮声不绝,我居民损失奇重。同时复以步兵冲出界外,进攻我保安队防地,我方仍以镇静态度应付,从未还击一炮。先日方又大举以海陆空进攻,我为保卫国土,维护主权,决不能再予容忍。时至今日,和平确已完全绝望,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御侮救亡,义无反顾。”[7] 也是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抗战自卫书》,8月15日,日本开始了全国军事动员,并成立作战大本营。淞沪会战历经三个月,与平津战役不同,日军在上海开辟的战线受到国军精良部队87师和88师的有效抵抗,陈诚、顾祝同、张治中、张发奎任战地指挥官,蒋中正兼司令长官。中方有70万军人,而日本陆、海、空军共计27万人,中日双方进行了寸土必争的殊死较量,战场中士兵“每小时的死伤辄以千计”(李宗仁),惨烈的程度让淞沪会战堪称“自从凡尔登战役以来这个世界所见过的最血腥的战斗”(魏德迈),国军伤亡25万人,有10名将军战死。最终,中国军队不敌日军于11月9日向杭州和南京撤离,李宗仁写道:“然前方此时已溃不成军,各军仓皇后撤,加以敌机日夜轰炸,人马践踏,秩序大乱。”[8]故中国军队在撤离中伤亡不少。之前林彪的115师于9月24日在山西东北的平型关对日军数百人的歼灭被视为中共指挥八路军的第一个胜仗,以后这场不大的战役被中共反复颂扬。11月20日,国民政府决定首都迁往重庆。12月13日,日军攻陷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日军在南京城实施大范围的血腥屠戮:纵火、劫夺、强奸与枪杀,有近30万中国人被害,造成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9]。24日,杭州沦陷,淞沪保卫战彻底告罄:
上海,南京相继失守之后,我国陆、海、空军的精华丧失殆尽。举国惶惶,凄惨景况难以言状。于是汪兆铭等主和派沾沾自喜,以为有先见之明,一时妥协空气甚嚣尘上,若非全国军民抗战意志坚强,实已不堪再战。 [10]
从8月《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署开始,苏联陆续提供了近3亿美金的低息贷款、上千架飞机和相应配置的2000名飞行员以及数百名军事顾问,参与了中国的抗日战争——斯大林的目的是通过支持中国抗日进而牵制日本军事力量以避免日军入侵苏联。
基于占领区需要日常维护与管理,日本开始在占领区内蒙、北平和南京寻求建立傀儡政权:1937年11月22日,日军将“察南自治政府”“晋北自治政府”“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合并为“蒙疆联合委员会”;1937年12月14日,将“北平治安维持会”“天津地方治安维持会”“河南省自治政府”以及“山西省临时政府”在北平合并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38年1月,当国民政府非常明确地表现出与日军长期抵抗的态势时,日本御前会议开始制定《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方针》,在以战争为主要手段的前提下,决定通过“扶助中国新兴政权”,以替代国民政府——或者并入新的政权,调整与中国的邦交。3月18日,日军将上海大道市政府(1937年12月5日成立)、南京自治委员会(1938年1月1日成立)和杭州治安维持会(1938年1月1日成立)在南京合并为“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以备“促进蒋介石政权实质性的崩溃”之需。在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之后,继续留在沦陷城市训练有素的行政官员不是失去作用,就是成为傀儡政权的各级官员和工作人员。

1938年2月,日军参谋部草拟《昭和军制建设纲要》,决定实施总体战体制,“毫无保留地统一部署国家的全部力量,并始终指导和动用它来贯彻战争目的。使用的手段,分为武力、经济、政治和思想四个方面,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但武力是决定性力量” [11]。
占领南京后,日军下一个目标是占领中国第五战区统辖的徐州,这里是津浦铁路和陇海铁路的交汇点,占领徐州意味着日军南北线贯通。1938年3月下旬,日军矶谷师团4万部队首先抵近徐州东北30公里的台儿庄,日军以飞机和坦克的攻击作掩护猛冲台儿庄,三天后日军进入台儿庄,守军总司令孙连仲指挥的第二集团军与日军在石块累积的房屋巷道中拼死激战。4月3日,全庄三分之二为日军占有,孙连仲与三十一师师长池峰城在第二集团军伤亡过十分之七时,仍然死守台儿庄,并通过组织敢死队分组向敌逆袭,夺回四分之三街市,黎明,汤恩伯军团赶到并从敌军后方围歼,第五战区的全面总攻,使日军伤亡二万人以上,矶谷师团主力被歼灭。发自台儿庄的捷报给国人巨大的鼓舞与信心,并让国际社会对中国军队和抗战重新认识。5月15日,南北日军共三十余万人对徐州形成包围之势,第五战区国军开始“有计划的撤退”(李宗仁),5月19日,日军占领的徐州为空城,徐州撤离军队没有出现像淞沪会战那样因仓促而导致的悲剧,军力得到保护。6月4日,日军攻击开封,两天后守军不得不撤离。9日,为抵御日军的急速进攻,蒋介石下令炸毁黄河河堤,洪水有效抑制了日军第十四师团和第十六师团,进至新郑的日军骑兵联队被国军全部歼灭,日军的军需及弹药物资的运输大大受阻,洪水泛滥也使日军的机械化部队明显失去效力。但同时,黄河的决堤导致民众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之后的灾荒与灾民流亡显然导源于此。
攻陷徐州之后,日军的下一个目标显然是武汉。日本大本营希望通过攻占武汉,逼迫国民政府投降。首都搬迁重庆需要一个过程,的确,重庆所处的西南地区在战时具有明显的地理优势——崇山峻岭、悬崖峭壁、江河川流且道路原始崎岖,因而成为抗日的后方基地。不过一开始,处于长江中游的武汉是首都搬迁至重庆时最早的军事和政治中心,郭沫若在回忆这段时期时有这样的表述:“南京的国民政府,国民党的中央党部,虽然都搬到重庆去了,但国民党的党政军方面的重要人物差不多都集中在武汉。在野的各党各派的领袖们,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也差不多都先后集中到武汉来了。武汉成为了事实上的抗战首都。”[12] 无论如何,随着战事的紧迫,全国各个高校、中等学校以及工厂纷纷内迁[13],平津的大学例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陆续迁徙内地,先是至长沙合并为长沙临时大学,之后又奉教育部命令迁往昆明,并更名为西南联合大学。部分平津学院迁往西安;东南沿海地区的高等学校如中央大学、复旦、交大等迁往重庆;最终,重庆、昆明、成都、西安和兰州,成为那些学院机构内迁与企业落脚的主要城市,仅仅是重庆就容纳了25所院校,这种战时的教育迁徙给八年抗战的中国留下了特殊的历史人文景观。
正是在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改组,中共的周恩来被任命为政治部副主任,这让人联想到国共第一次合作的情形。在与国民党的第二次合作中,中共采取了党的组织和成员仅仅部分公开,而大部分隐蔽的党员继续进行地下工作的策略,这样做的目的是应对政治形势任何可能的变化。国民党将政治部第三厅交给了中共成员来操持,以致第三厅成为中共宣传抗日发动群众的一个有效阵地。1938年3月29日,国民党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除了决议蒋介石为国民党的首任总裁、建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和通过《抗战建国纲领》外;设立国民参政会作为战时国家最高民意机构是民众普遍关心的重点,当包括中共在内的不同党派或持不同政见的人士都参加进了于7月7日至15日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参政会成立大会时,人们将视其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措施,因而受到了非常大的鼓舞。军事安排上,6月14日,国民政府在武汉卫戍司令部的基础上组建第九战区,陈诚被任命战区司令。7月25日,在海、空军的掩护下,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的部队开始了对九江的总攻;9月29日,田家镇要塞被日军攻陷;10月初,日军第106师团被国军第二兵团司令薛岳将军的部队几近歼灭,然而最终,中国军队于10月中旬撤离武汉:之前从6月开始,武汉民众、政府机构以及军事机关就开始撤离,重工业和军工业不能够撤走的都做了破坏。10月21日,日军坦克已经进入给武汉输送物资的城市广州;10月26日,武汉沦陷。武汉会战的战场覆盖范围包括江西、安徽、河南和湖北,中国军队有120个师参与,日军投入兵力12个师团,加上补充的力量共计40万军人,在武汉会战中,日军死伤20万余人。虽然武汉失守,形势非常严峻,中国此时仍未得到国际社会的及时援助,但是,日军的战线显然已经过度延长,当初希望三个月内完成中国战事的计划完全落空。截至武汉会战,日本投入中国内地兵力26个师团,日本国内仅仅剩下一个近卫师团。蒋介石于10月31日发表《武汉撤退告全国军民书》,他要人们以“更哀戚、更悲切、更踏实、更刻苦、更勇猛奋进”的精神坚持“持久抗战与全面抗战”。
注释:
[1] 主要成员有海军大尉塚野道雄、海军上尉三上卓以及另外三位海军尉官及八位海军预备役尉官共计20人。
[2]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由于工业的发展而需要原材料和市场,对亚洲及其资源的觊觎是人人皆知的,“绪言”里已经涉及日本对朝鲜的发展(1875年)、日俄在中国领土的战争(1904-1905年)。对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的占有(1914年),如此等等。
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身为陆军大将的田中义一首相兼外相在东京外相官邸主持了“东方会议”,他召集了日本军政要员研究讨论了涉及中国的“大陆政策”。会议集中到使满洲脱离中国版图,置于日本控制并由日本参与其主权这个主题。会后,田中完成了会议文件《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密奏天皇,谓“田中奏折”。“奏折”中有这样的文字:
所谓满蒙者,乃奉天、吉林、黑龙江及内外蒙古是也,广袤七万四千公里,人口二千八百万人。较我日本帝国国土(朝鲜及台湾除外)大逾三倍,其人口只有我国三分之一。不惟地广人稀令人羡慕,农矿森林等物之丰富,世之无其匹敌⋯⋯故历代内阁之施政于满蒙者,完成新大陆政策。
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
倘中国完全可被我征服,其他如小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
1931年,政友会议员松冈洋右(他也是以后的甲级战犯)在众议院上说:“我认为满蒙问题是关系到我国生死存亡的问题,是我国国民的生命线。国防上经济上必须这样考虑。”
参与“9.18”事变策划的板垣征四郎在他的《从军事上所见到的满蒙》写道:“在对俄作战上,满蒙是主要战场;在对美作战上,满蒙是补给的源泉。从而,实际上,满蒙在对美、俄、中的作战上都有重大的关系。”
1930年底,日军情报部长建川美次召集策划,提出《一九三一年度形势判断》,提出解决满蒙问题的三个阶段:1,打破现状;2,建立亲日政权;3,完全占领东北。1931年6月,建川以参谋部作战部长的身份召集会议制定了《解决满洲问题方案大纲》,涉及到如必要将“立即采取军事行动”。
1935年5月1日,日本政府修改《帝国国防方针》和《帝国用兵纲领》,谓:“对中国作战的初期目标,是占领华北要地和上海附近,保护帝国权益和日本侨民。”
1935年6月3日,日本陆军部制定《昭和十二年(1937)度的对华作战计划》,其中有关于对华作战的具体安排,任务目标是:“在三个月内,使中国丧失全部抵抗能力,达到速战速决的目的。”
1936年,日本陆军建设发展完成,日本主张军事扩张的财阀和军阀势力也逐渐占有上风。
1937年1月,日本关东军制定《满洲产业开发五年计划纲要》;5月29日,日本陆军省制定《重要产业五年计划纲要》,资源范围涉及中国东北和华北。
[3] 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日本为了保护租借地和南满铁路,建立了关东军。1928年,出于对满洲的控制,关东军总部从大连移至沈阳,一是企图获取满洲的控制,同时也针对苏俄可能的南下。
[4] 1935年,国民政府已经考虑将四川、贵州、云南作为抗日后方基地;冬,蒋中正指令张治中建筑上海和南京地区的战地工事;1936年,国民政府对日作战军事部署拟定完成。
[5] 指7月8日中共发表的抗战宣言。
[6]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302页。
[7] 《张治中回忆录》(上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第122页。
[8] 《李宗仁回忆录》(下)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96页。
[9]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对“南京大屠杀”有这样的认定:“中国军队在南京陷落前就撤退了,因此所占领的是无抵抗的都市。接着发生的是日本陆军对无力的市民,长期间继续着最恐怖的暴行。日本军人进行了大批屠杀、杀害个人、强奸、劫夺及放火。尽管日本籍的证人否认曾大规模进行残虐行为,但是各种国籍的、无可置疑的、可以凭信的中立证人的相反的证言是压倒有力的。这种暗无天日的犯罪是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占领南京市开始的,迄至一九三八年二月初还没有停止。”
[10] 《李宗仁回忆录》(下)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00页。
[11] 转引自李庆山:《正面战场抗战真相》华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93页。
[12] 郭沫若:《洪波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0页。
[13] 香港《工商日报》(1939年6月10日)有一个统计:
统计目下已迁移至川、滇、湘等省之工厂,已有三百余家,此种工厂,约可分为九大类,即采矿、电机、无线电、化学、罐头、陶瓷、玻璃、印刷文具、五金、纺织、皮革等,其分布之比较,约为四川占百分之四十四,湖南占百分之三十九,广西占百分之六点九,陕西占百分之六点五,其他云南贵州各占百分之三点六,除军事工业品有相当产出外,其他各种日用品工业品,出产量均有增加,目下川、滇、湘、桂、赣、陕各省地方人民所需用之日用品,皆由国内工厂之出产品供给,质的方面亦有相当改良,此实为抗战后国内工业改进之良好现象。